|
林凤眠生平 要想通过一篇小文来完整地勾勒出林风眠,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在近代的中西融合派画家中,林风眠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作为中国近代两所国立艺术学府的执掌者;早年曾风风火火地提倡过“走上十字街头”的艺术运动,而晚年却似乎截然相反地回到艺术的“象牙塔”;加上他画中所流露出的那种难为人道的宁静气息……这一切,都为他的一生添上几许神奇的色彩。 梦开始的地方 一条清澈的小河缓缓地流过宁静平凡的小古镇,每当到了岸边槐榉树开花的季节,黄色的花儿就像梦中的符号一般飘落在小河中、路径上……。1900年11月22日,林风眠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古镇上--广东省梅县(古称嘉应州)白宫镇阁公岭村。对于幼年的林风眠来说,当带着他上山打石头的祖父任其在山林草丛中玩耍时,故乡那"并不特别美丽"的风貌却由此赋予了他爱好自然之美的心灵。祖父林维仁曾告诫小孙子:"脚下磨出来的工夫,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老人朴素、勤勉的形象直到晚年仍深深地印在画家的记忆中。父亲林雨农也是传统的石匠手工艺人,不过,除了会刻石头外,父亲还会在纸上画几笔,这让林风眠从小就对绘画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并按着《芥子园画谱》自习不缀。 15岁时,林风眠考取了省立梅州中学,在此期间,他和日后的好友林文铮、李金发等一起组织了一个“探骊诗社”。切磋诗艺,并任副社长,“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昭明文选》是他课余最爱读的书。对于绘画,他更为迷恋,当林风眠的亲戚从南洋带回来一些印有外文插图的小舶来品,那种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画风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林风眠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当时,林风眠的绘画成绩深得绘图教师梁伯聪的赞赏,这位我们知之甚少的老先生发现林风眠形象记忆能力特强,图画过目不忘,并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创造。梁老先生认为学生画得和自己一样好才能得100分,而却经常在林风眠的图画作业上打120分,对林风眠的欣赏有此可见。 20世纪20年代,正值中国青年学生的留洋运动热潮,1919年7月,中学刚毕业对前途感到彷徨的林风眠收到了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林文铮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对欧洲艺术有着美好憧憬的他遂告别父老前往上海和林文铮一同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登上了法国邮轮奥德雷纳蓬(Andre le Bon)号,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求学之路--实现梦想的路。 欧洲游学 1920年1月,奥德雷纳蓬号抵达了法国的马赛港,随后在安排下林风眠一行进入枫丹白露市立中学进行法文补习同时以学写招牌油漆工的收入维持生活。 1921年,林风眠和李金发一起转入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Ecole Nationale des Beaux-Arts de ijon)这所位居法国六大国立美术学院榜眼之位的高等美术学府学习,他的才华深得校长耶西斯Yencesse)的器重。9月,在耶西斯的推荐下,林风眠和李金发又一起转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es Beaux-Arts)就读,并得以进入被时人誉为“最学院派的画家”柯罗蒙(Cormon)的工作室学习,幼年对西方绘画的憧憬使林风眠一度完全沉迷于细致、写实的自然主义学院派画风中——“自己是中国人,到法后想多学些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所以学西洋画很用功,素描画得很细致。当时最喜爱画细致写实的东西,到博物馆去也最喜欢看细致写实的画。” 不久耶西斯专程来看望这位学生,这位深受现代派和“东方艺术”影响的浮雕艺术家对林风眠提出了严厉而诚恳的批评:“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你到巴黎各大博物馆去研究学习吧,尤其是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学习中国自己最宝贵而优秀的艺术,否则是一种最大的错误。”同时他还告诫这位有才华的学生:“你要作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部门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这促使林风眠迈出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重新发现“东方艺术”的魅力,并关注起现代主义艺术。从此,巴黎的卢浮宫、东方美术馆、陶瓷博物馆中经常出现林风眠瘦小的身影,在这些艺术殿堂里,林风眠啃着面包、拿着画具仔细地研究,他了解到欧洲艺术最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努力地从中汲取艺术的营养。 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无论对耶西斯还是林风眠而言,所谓的对中国艺术优秀传统的理解都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20世纪初的欧洲画坛,正是表现主义等现代派艺术开始盛行的时期,而现代派艺术一开始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东方艺术的某些因素,诸如边角式的构图、对线条的强调、对比强烈的色彩等。更为重要的是,“东方”这个概念在当时的欧洲有着极为广泛和模糊的概念内涵,所泛指的是非西方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理解也是停留在这个概念上的,这就必然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某种“误读”,尽管这种“误读”后来却“阴错阳差”地造成了林风眠独特的个人艺术面貌。 1923年春天,在同乡熊君锐的邀请下,林风眠与李金发、林文铮、黄士奇等开始为期近一年的德国游学,这一年的游学生涯对林风眠的早年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游学中充分地接触了当时作为新艺术风格形式出现的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新绘画流派,尤其是对自然主义强烈反动的表现主义,林风眠更是毫不犹豫地以一个中国留学生特有的方式接受了它,他要用线条和色彩去表现他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一年相对自由的时间使之创造了大量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的作品,像著名的《柏林咖啡》、《平静》、《唐又汉之决斗》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都具有当时典型的现代表现主义风格特征:鲜明的主题、强烈的笔触、沉郁的色彩,画面充满着年轻画家的诗情幻想和浪漫热情,达到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高峰时期。 德国的游学也为林风眠带来爱情女神的眷顾,在柏林的马克兑换市场上,林风眠邂逅了一位温柔善良的德国姑娘艾丽丝·冯·罗达(Elise Von Roda),这位柏林大学化学系的女大学生浪漫多情,爱好文学和艺术,并把林风眠引入了缪斯之神的殿堂,罗达为林风眠弹奏的乐曲让他永生难忘。从此,音乐成了林风眠毕生的爱好。1924年初,林风眠带着他大量的作品和心爱的姑娘回到了巴黎,在玫瑰别墅六号的一所公寓内与罗达小姐结为伉俪。 初识蔡元培 回到法国之后,带着新婚的浪漫,林风眠立刻投入到创作中去。他和刘既漂、吴大羽、林文铮、王代之等就组织了一个强调美术学理研究的绘画沙龙组织--"霍普斯会","霍普斯"(Phoebus)的含义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在欧洲古典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主宰光明、青春和艺术,无疑这一名称具有隐喻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方向的双重含义,正表现了青年林风眠为世人创造有生命的艺术的信念。1924年二月,"霍普斯会"联合另一个旅法艺术团体--美术工学社(注重美术工艺制造的研究)发起成立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办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并特邀当时正旅居斯特拉斯堡的蔡元培为名誉会长。5月21日,"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正式开幕,在这个"巴黎各大报,几无不登载其事"的展出中,林风眠展出了包括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在内共计42幅作品,并被法国《东方杂志》记者评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 林风眠的展品中有一幅游学德国时所作的《摸索》,这幅仅花了作者一天时间一气呵成,“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且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藏于笔端”的作品吸引了蔡元培的注意,《摸索》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历代伟人探求人生真谛的精神,正和蔡元培“美育代宗教”、“教育救国”的思想相吻合。经介绍,他认识了当时还只有20岁的林风眠,对这位才华横溢、品德优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画家极为欣赏,闭幕后他还特意偕夫人周养浩一起来去玫瑰公寓拜访林风眠,这仅仅是他们的第一次相交! 1924年秋,对意气奋发的林风眠却犹如一个噩梦,心爱的夫人罗达分娩后不幸患病死去,而新生的婴儿也随即夭折,这对深情的林风眠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在悲伤的心情下,他没日没夜地凿刻着爱侣的墓碑,在上面刻下了自撰的碑文,以此作为永生的纪念。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伤心的他力图将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心爱的艺术。 1924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林风眠的《摸索》和《生之欲》两幅作品入选,《生之欲》所画的是四只老虎从芦苇呼啸奔夺而出,命题用了哲学家叔本华的名句“众生皆有生之欲”,形式内容都依然是表现主义风格的,但在具体技巧的运用上,则用了中国水墨绘画淋漓尽致的表现手法,这无疑是林风眠早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作品,体现了他力图把“东方艺术”的“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形式溶为一体的艺术主张,正和蔡元培在斯特拉斯堡展览会上所发表的“学术上调和与民族上调和”一文的宗旨相合。1925年的巴黎国际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博览会上,当蔡元培在中国馆中看到这幅虎图时,高兴地赞叹道:“得乎技,进乎道矣!” 1925年4月18日,林风眠和第戎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爱丽丝·法当(Alice Vattant)结婚。或许,再次的婚姻让本性浪漫的林风眠又多了几分成熟,为了摆脱对罗达的思念,他和新夫人搬到了第戎城外的乡下,历经了幼年的启蒙教育和欧洲的求学探索,林风眠不再只是个寻求梦想的热血青年了,他正有一种将梦想变为现实的迫切愿望,而祖国的热土才是实现梦想的地方。1926年,受蔡元培的聘请,林风眠接受了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职,携带妻子踏上了归国的创业之路。 年轻的校长 由我国近代教育界领袖蔡元培于1918年所创立的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一所美术学校,1922年更名为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改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设音乐、戏剧两系。1926年国立艺校因为学潮风波决定由学生自己投票选举校长,由于蔡元培的鼎力推荐和前期回国的王代之的大力宣扬,林风眠以得票数第一被国民北京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艺专校长--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 1926年3月1日,归国后仅在上海逗留了几天,风尘仆仆的林风眠就赶赴北京就任。对于天真浪漫的林风眠而言,不管这所学校的现状如何,现在却是他实现"融合中西艺术"、"艺术救国运动"理想的最佳土壤。当时的北京艺专,由于刚经过学潮风波,几乎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林风眠到校后首先做的就是重新建立完整的教学班子,他热情挽留住了刚提出辞呈的教授肖俊贤、谢阳、冯白、彭沛民;又请回了先前被辞退的陈师曾、吴法鼎、李毅士等五位教授。当时一批有实力的文艺人士如郁达夫、余上沅、熊佛西、黄怀英、萧友梅、周作人、谢冰心等都曾在艺专任教或兼课。学生中也有不少优秀的人才:刘开渠、李苦禅、李有行、雷圭元、冼星海等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融合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林风眠还特地邀请当时还只能算是个“乡巴佬”的齐白石和法国画家克罗多(Claudot)来校讲学,希望齐氏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氏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绘画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培养出大批适应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 1927年5月11日,由林风眠发起并组织的“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此次展览采用了克罗多的建议,取消了中西画和图案的界限,2000多件作品以混合式的陈列方式展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的艺术大展,其形式原拟仿照法国沙龙,成立代表大会审查委员会评选作品,但终因门户之见太深而取消, 这便使艺术运动的效率也因之减少。林风眠在大会开幕式上演讲了《艺术大会的使命》一文,表达了大会的宗旨:“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而艺术大会的口号就像战士走上战场前的宣言:“打倒模仿的传统艺术!打倒贵族的少数人独享的艺术!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全国艺术家联合起来!东西艺术家联合起来!人类文化的倡导者世界思想家艺术家联合起来!” 年轻的艺专校长林风眠这时象一个浪漫的自由主义战士一样,希望通过艺术运动的冲击来改变现实的黑暗,可是,当时的文化经济环境、政治的干预和人们的不理解注定这次艺术大会只能是一幕壮烈的艺术运动悲剧,艺术大会最终流产的结果使充满热情的林风眠感到失望”不期横逆之祸,不先不后,偏于此艺术运动刚有此复兴希望时来到,于是费尽多少心血,刚刚扶持得起的一点艺术运动的曙光,又被灭裂破坏以去!这是艺术运动中多么可悲的事呵!" 然而,暂时的挫折并不能浇灭林风眠心中的火焰,他决定以“决然的态度,向新的方向,继续努力。”1927年7月,林风眠愤然辞去了北京国立艺专校长职务,受蔡元培的邀请,南下就任南京中华民国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归国后最长的一篇言论《致全国艺术界书》,他回顾了自己的得失成败,剖解了中国的艺术现状,并提出了:“我悔悟过去的错误,何以单把致力艺术运动的方法,拘在个人创作一方面呢?真正的艺术作品的产生,与其新生的影响,自然很大;如果大多数人没有懂得艺术的理论,没有懂得艺术的来历的话,单有真正的艺术作品,又谁懂得鉴赏呢?”“从此,我们把艺术运动的信条,于努力力行之外,更须加上宣传一项”。同年年底,林风眠受委托负责筹办“国立艺术大学”的事宜,当蔡元培在迷人的杭州西湖畔选定了民国政府的最高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的地址时,林风眠再次被任命为校长兼教授。可这次,还会是一幕悲剧吗? 西子湖畔,新艺术的摇篮 1928年4月8日,国立艺术院(1929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美丽的西湖罗苑补行了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然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正如国立艺术院组织法中所述:”本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杭州艺专的教育方针秉承了林风眠的一贯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不过,林风眠也吸取了北京国立艺专的教训,他认识到要办好自己的学校,贯彻自己的教学主张,就必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优秀的教学队伍,当时林风眠任校长兼教授、林文铮任教务长,克罗多任研究部导师,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潘天寿为中国画系主任、李金发为雕塑系主任、刘既漂为图案系主任、王代之为艺术院驻欧洲代表;其余象蔡威廉、潘玉良、李风白、方干民、李苦禅、刘开渠、姜丹书等,都是当时的骨干。中国现代绘画史上一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大量优秀艺术人才的现代教育模式的艺术学院正是在这批艺坛精英分子的努力下开始成长的。 当然,不同的分歧还是有的,最著名的就是林风眠和潘天寿两人关于是否合并中、西两系于一的争议。对于一直以调和中西艺术为己任的林风眠而言,只要能达到创造时代的新艺术,通过新艺术来改造社会,那么中西两种艺术最终该混为一体,至少在教学的体系上不应该"视国画与西画有截然不同的鸿沟,几若风马牛之不相及"而"两系的师生多不能互相了解而相轻,此诚为艺术之不幸!"而潘天寿则持相左意见,他著名的论点就是将东西绘画体系比喻成两座独立的大山,两座大山间,是可以互相取其所长的,但如果是随便的吸收的话,则只能是各取所短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林风眠关心的是东西两种不同艺术体系的共性,而潘天寿更为关心的是不同艺术体系的个性,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当时每一个涉及于此的艺术家所不能避免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呈现出纷乱的多元化,再加上每个艺术家生活经历、对传统和西方文化理解的差异,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也正显得合情合理的了。 不过,林风眠最为关心的还是艺术运动。为进一步深化艺术运动,1928年来林风眠组织策划成立了“艺术运动社”,考虑到在艺术创造的力行之外,"更须加上宣传一项",“艺术运动社"还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相关的杂志--《亚波罗》和《雅典娜》,巴黎"霍普斯会"的艺术运动精神在西子湖畔浴火重生了。这个以艺术改造人生,艺术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群体,曾意气风发地说:”西湖可能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1930年,林文铮为新学院谱写了新校歌:“莫道西湖好,雷锋已倒。莫道国粹高,保叔倾凋!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不有新艺宫,情感何以靠?艺校健儿,齐挥毫横扫!要把亚东艺坛重造,要把艺光遍地耀!”,所表达的正是一种激昂的艺术运动精神。杭州艺专的一切,和林风眠在北京艺专时相比有较大的进步,林风眠的艺术之梦似乎就要实现了。 艺术与人生 在谈及林风眠的文章中,都不应该回避杭州艺专“西湖一八艺社”的故事。林风眠在创建“艺术运动社”的同时,艺专内的学习气氛浓烈,各种学生自发的团体组织纷纷建立,“西湖一八艺社”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但它的著名并不是在于创造了多么不朽的作品,而是它的分裂。 1930年春天,“西湖一八艺社”在上海举行了首次的公开展览,在展览的座谈会上,对美联许幸之提倡的“普罗”美术的口号,一部分社员表示了反对,反对的原因是“普罗”美术的提法违背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宗旨,而另一部分“普罗”美术的支持者们则略去了“西湖”二字,挟“一八艺社”的遗号,汇 入了鲁迅刚刚在沪上掀起的新一轮不同宗旨的艺术运动。在这群坚信“为人生而艺术”的同志中有陈卓坤、于海、陈铁耕、后来牺牲的姚夏朋和曾为林风眠破格录取并搭救过的张眺,以及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最终弃画从诗的艾青等。 “西湖一八艺社”的分裂,从表面上看,是“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两种不同的艺术观点的对立。这种对立,从这两种观点在欧洲大陆诞生的那一天就有了,林风眠在北京开“艺术大会”的时候,也发生过碰撞,他还为此专门撰写了《艺术的艺术与社会的艺术》一文力图折衷调和。 按理来说,提倡"普罗"口号的"一八艺社"所宣扬的宗旨应该与林风眠一贯坚持的“艺术救国”思想更为一致,它们都力图将艺术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殊途同归。可是,对于认为“艺术根本系人类情绪冲动一种向外的表现,完全是为创作而创作,绝不会想到人类的功用问题上来。”的林风眠而言,在他的梦想中,所谓的"艺术救国"是想通过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唤醒国土上广大人民在文化上的理性和觉悟,"人生需要面包,人生还需要比面包更重要的东西-艺术呢"。这实际上是要求用更高的文化素质标准用于平民。在这个意义上,"为艺术而艺术"是有积极甚至革命的意义的。 然而当时的情况下,社会革命比起艺术救国来毕竟要来得更为直接和彻底,而所谓的“为人生的艺术”正是一种最终服务于社会革命的艺术观点-并不是把平民的文化素质提高到艺术的标准,而是通过平民能够马上理解熟悉的形式宣传某种功用问题为目的,流弊所至,以至于任何“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艺术形式,都成为颓废的“象牙塔”艺术了。 如果说“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话,那么"为人生的艺术"的观念就是现实主义的。“西湖一八学社”的分裂实质正是现实社会和艺术理想之间的矛盾,双方互为指责:一方粗鄙、无修养、另一方空虚、无聊。尽管“为人生的艺术”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可今日中国文化艺术的混乱和缺乏理解的现状,总让人心头有着沉重的压迫感。或许,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真正的悲剧是双方都没有做错事。" 林风眠的梦又破灭了,他所向往的艺术运动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林风眠终于逐渐开始趋于沉默,他对于“一八学社”抱着既不支持、亦不反对的态度,尽管他也曾为“一八学社”举办的展览题写过文字,也曾数度出于自己宽厚的本性帮助过被捕的学生,但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政治上,都对学生们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前者体现的是林风眠的“学术自由”精神,后者却多少反映出了林风眠自己在政治及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上的困惑状态。林风眠的性格正在发生着变化,他的兴趣,从过去致力于艺术改造社会的进步转移到专注于艺术的变革上来。 风眠体的诞生 1937年,林风眠在苦心经营的杭州艺专已度过了十个春秋。一年前,代表着林风眠“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出到第17期终于不再出版了,对于来林风眠来说,这是他一个时期的结束,也是亚波罗精神的终结,从此,改造社会的艺术运动对于林风眠而言,已不再是他的梦想了。象征着进取、热情的亚波罗精神被平静、深沉的悲剧精神所代替,这种精神的实质正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所写到:“因为你,虽饱经忧患,却没有痛苦,以同样平静的态度,对待命运的打击和恩宠;能够那么适当地调和感情和理智,不让命运随意玩弄于指掌之间,那样的人才是真正幸福。”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风眠体正是这一有如月光一般冷凝的悲剧精神的艺术反映。 1937年,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一年,在当局的命令下,林风眠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建立的学校,带领全校200多名师生和大量的图书教具,汇入难民的大潮,向西南后方转移。1938年,杭州艺专和同样逃难于斯的北京艺专合并,成立了抗战时期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后的学校,采用委员制而废校长制,由于经费、教育方针、人事等众多问题,校内的各类矛盾时常发生。而有谁能想到,这两所林风眠都任过校长的学校的合并,却最终导致他辞去校领导的职务。 不过,这时的林风眠对这些累人的琐事已感到越来越厌烦了,经历了最后的两次"倒林"风波后,他终于离开了国立艺专。 艺术运动的梦碎了,尽管林风眠后来也会偶尔说:“与世隔绝起来,新艺术运动的担子交给谁?”的话,这,毕竟只是一种感伤怀旧的情结所累。然而如果以为林风眠就此放弃了艺术的追求,那就错了。另有一个梦,从林风眠踏上欧洲的土地时就一直没放弃过,那就是对于中西艺术的汇通与融合。 从国立艺专隐退下来后,林风眠开始了在重庆嘉陵江畔的艺术探索生活。从具体的形式上而言,大体可归纳为"方纸布阵"的画面布局和对传统"笔墨"观念的改造。对于这种新艺术形式探索的评价,随着近年来画坛林风眠热的而颇有成果,小文就不多加评述了。简单地说,林风眠的中西融合更多地体现在观念上,他由学习西方自然主义转而服膺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方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因而他试图用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观念来切入中国绘画,同时,林风眠的留学时间大多消磨在东方博物馆的陶瓷作品上,造成了他作品中技术成分的缺失,在林风眠的作品中,中国画赖以生存的骨线被抽去了"笔墨"的特质,同样地,黑色在他的作品中也仅仅被当作一种色彩来看待而失去了在传统中国画中具有的特殊意义。这也造成了他的画从外观上看更像西方画,从而被人误解为不传统。但是从作品的内涵来看,那种冷凝的悲剧精神在画面上的升华,使之更为锲合中国画"心画"的纯粹性,独具一格的林氏画风-风眠体终呈现在世人眼前。林风眠曾一度为自己的画还算不算中国画而苦恼,在如今看来,这种苦恼完全是多余,因为林风眠对于绘画观念的重视已足以使其创作在当时的时代具有渡世金针的作用,从而成为标领时会,开资后学的一代新风。 林风眠关于中西融合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笔墨观念,同时开启了对于诸如形式、材料等方面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中国绘画的创作面貌,为众多后继者诸如吴冠中、赵无极、刘国松等提供了可借鉴、深入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实在可算作是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启蒙者。 尾声 从1937直到1991林风眠去世为止,在50多年的时间里,林风眠大多数时候过得都是半隐居式的生活,除了在艺术的探求上一如既往地投入热情和心血外,他对其他事都显得不那么地关心,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唯唯诺诺。经历了过多的政治经济事件,对于名声和荣誉,他已看淡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林风眠最终放弃了他曾经执着过的艺术救国、美育代宗教的理想,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使他的梦想一次一次地破灭了,但他对近代中国艺术的影响却不能说是消失了,而是以他独特的艺术形式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他象他祖父那样在艺术园地里勤勉地"笑谈风月,但问耕耘" 小文到这里想告一段落了。正如一开始所言,要想全面地了解林风眠,这短短的一篇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在近代中国的艺术史上,林风眠无疑会最终确立自己真正的位置,而现在我们对于艺术文化的展望或许正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中写的那样:“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而孩子回答到:“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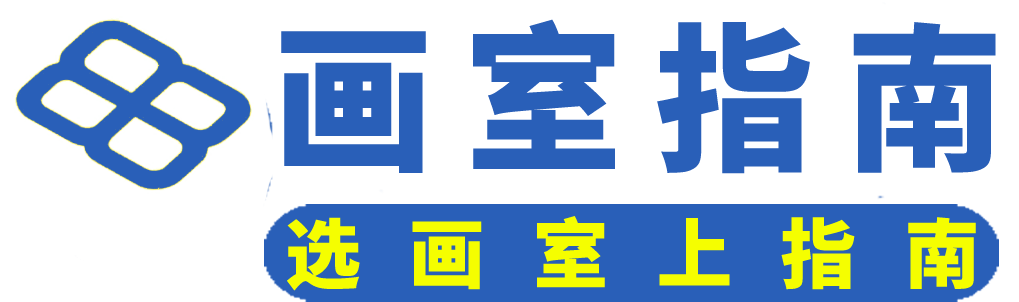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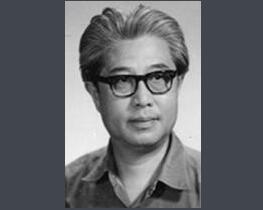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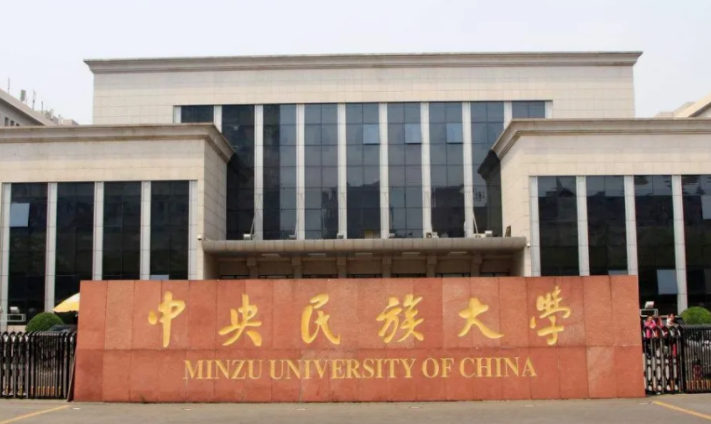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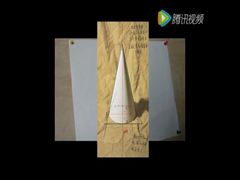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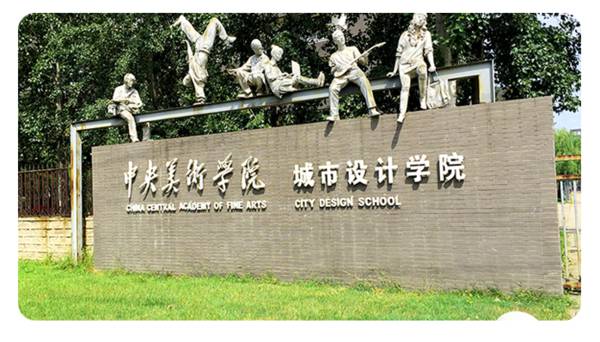













 谢老师
谢老师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